傍晚,在隔離酒店無所事事,眺望這座疫情之下的都市。這是馬來西亞的首都,曾是最繁華的商業街。
可疫情仍在持續,寬闊的大街如死寂一般,寬闊的馬路只有寥寥幾輛行車,紅綠燈罷工已久,人行道也只剩下行色匆匆的外賣員。整個城市都寂靜了,只有海水拍打著這島國。
我靠在窗前的躺椅,開始思考,這繁華一時的都市不復存在,頃刻之間淪為死寂一片,哪什么又是永垂不朽的呢?想著想著意識開始恍惚,燈光明暗交織,慢慢地將我的記憶帶到了許久之前……
那好似家鄉,一家人正享受著晚飯后的閑暇,驅車至江邊,捕捉著江邊的晚風和紅霞。晚霞映照在江面上,晚風將一陣又一陣的浪花吹得翻滾,前仆后繼地拍打兩岸,似乎合奏著,吟唱出一首哀婉感人的歌曲。
奉節白帝城下,夔門如青銅屹立。滾滾江水,前赴后繼,涌入夔門,奔騰不息。秋風過處,瑟瑟作響。一位清瘦老者,面對蒼山,悄然佇立。寒風撩起他的白發,他卻全然不知。他正在吟誦那千古不朽的名句:“風急天高猿嘯哀,渚清沙白鳥飛回。無邊落木蕭蕭下,不盡長江滾滾來。
里悲秋長作客,百年多病獨登臺。艱難苦恨繁霜鬢,潦倒新停濁酒杯。”無盡的長年漂泊之苦、綿綿的老病孤愁之感,盡在其中。
杜甫的生命,已經化作塵埃,然而,他的生命卻在詩句中延續,和長江一樣,萬年永恒。
大江之南,石頭城下,六朝繁華灰飛煙滅。一位詩人,一位有著硬骨頭又多愁善感的詩人,劉禹錫,在慘淡月色下,悄然登上荒草無邊的城墻,面對無語的大江,禁不住感慨萬千:“山圍故國周遭在,潮打空城寂寞回?;此畺|邊舊時月,夜深還過女墻來。”
是的,山圍得周遭嚴密,似乎還可以令人聯想到當年虎踞龍盤的模樣;但是江潮的拍打和退回,見到的只是空城,已經不知當年的燈火樓臺、徹底歌舞的繁華為何物了。秦淮河東面,那輪由古照到今的明月,想必領略過昔時那種醉生夢死的繁華的;但,它自東方升起,可待到夜深,也只是清光飄零地從城垛上照進城來。
一位才華絕世的詩人,在一個深秋的夜晚,在大江之濱,慷慨地給后人留下了這不朽的詩篇!
大江之中,皓月當空,陣陣涼風吹過,撩起了蘇子的衣襟,也撩動失意人的內心。面對這即將逝去的時刻,蘇子不禁吟唱:“駕一葉之扁舟,舉匏樽以相屬。哀吾生之須臾,羨長江之無窮……”道不盡的時光飛逝,道不盡的貶謫憂傷!然而,蘇子畢竟是曠達之人,他很快又大聲吟誦起來:“……且夫天地之間,物各有主。茍非吾之所有,雖一毫而莫取。惟江上之清風,與山間之明月,耳得之之而為聲,目遇之而成色。取之不盡,用之不竭。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,而吾與子之所共適。”
人生難免失意,蘇子在逆境中悲而不傷、泰然處之,將惆悵化為流水。這讓他與長江一起不朽。
漫漫歷史,悠悠長江,橫跨長江的得意之徒,東流或西去的飛黃騰達之輩,不可勝數,但能與之不朽的,又有幾位呢?人生短暫,須將生命的真諦融入長江,方能與之綿綿不絕,永垂不朽!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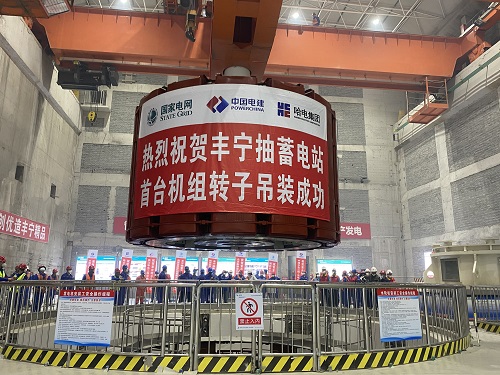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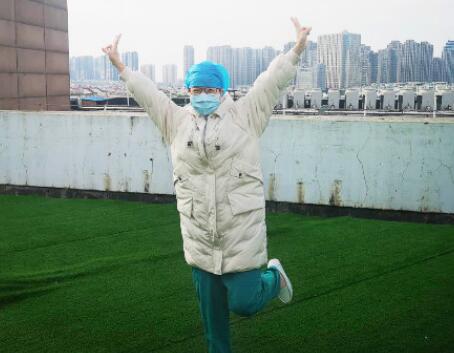



評論